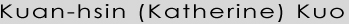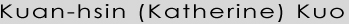近日來,藝術評論越來越頻繁,經常評斷藝術品華而不實和煽動人心,也批評藝術家為了彰顯流行文化的迷戀、明星的光環,以及為了滿足消費者的慾望,利用驚人的技倆創作出帶有娛樂性的作品。人們經常談論藝術正迷失它原初的宗旨。在此欣慰地出現一位藝術創作者,她以緩和、細緻的手筆,牽引藝術回歸它原初的價值和目的。而甚麼是價值和藝術目的?
經典的藝術應該是公諸於世,記錄每一年代人類心智的演進發展,也應該是人類歷史最優秀的典範,因為我們從文字、圖像記載中可以了解什麼是人類的精進和偉大。我們唯一的世界已經充滿著醜陋的政治面目,和每日戰場上殘酷、悲慘的事實。藝術帶給我們應該是關心和夢想,而且應該是: 「我們可以不必是如此,我們可以做出更好的一面。」但不幸的是,今日太多的藝術品與其反應令人害怕的,不如呈現一些新的創作給大家,甚至出自自大的觀點,通常這般藝術終究毫無意義,完全失去了實踐另一重要的藝術目的 ─ 那就是和全體的人性溝通。
以上的論述不適合套用在郭冠忻本人或是她的繪畫裡。二十年來,郭的作品從超現實主義到抽象表現主義,創作出多方面派別。她早期的作品,畫幅尺寸較小,畫中如夢境敘述著神化故事和神秘形體。今日,她的畫布比以前更大些,實質上,可以認同的形體已經消失了。她目前的繪畫重點在顏色,而這些豐富的色彩陣容已經取代她過往的表現手法。畫布上呈現出細緻的色調變化,使得觀者幾乎難以辨識。從她的廣泛作品裡,出現了一個問題:應該將郭的作品歸入哪一派別?其實這正好說明了觀者必須是以開放的思想,却不帶任何的偏見,親自來看她的畫。
郭的繪畫傳遞認真的訊息。觀者經常談論看見她的畫之時,畫能給人彷彿置身於教堂的感覺。畫面呈現寧靜與冥想,散發出令人舒緩的聲音以及流露出一份精細的力量,這力量可以激發人心去想像完全不同的世界,而且讓人們連繫更內在、深沉的自己。
郭說:「我一點也不在乎現在流行的方向;然而,我也不太順應今日社會的要求。在我的畫裡,我簡單地畫出我所感受的事物,誠實做自己。」
郭畫出具有形似十九世紀印象派時期畫家的風格。印象畫家表現當時特殊轉瞬間的光影、場景,然而郭畫出當下的感受。實際上,外在的環境有太多能夠構成一幅畫面的題材,如今,郭呈現給觀者的,却是來自她的內在體驗。
郭說:「當我勾畫自然風景時,畫面上呈現不只是單一的山、海洋、天空、樹林等實情,却是因為受到當時特殊的環境影響,從中由感而發的表現。」
她不是有意反對今日的藝術潮流,和概念藝術走上相反的方向,只是郭的作品不像概念藝術一樣,強調大腦的活動並將其重點放在點子與觀念上。
郭說:「日新月異的今日科技,不斷地分析快速、永無止境的數據,似乎我們的腦袋活著比過去更辛苦。我想我們的腦袋需要跳脫這喋喋不休的數位資訊,休息一下。在此,我的作品即為一種挽救。
「對我而言,思想混淆世界的亂象。所以,我的畫面說:「等一等,如果我們不去理會思想,而做些不同的改變、超越,看看會發生什麼?」
思想是概念藝術的所有。然而,經典的藝術應該是交集心靈和思想,卻不是腦袋。在作品裡,若一位藝術家放入太多的點子或是複雜的技術,點子和技術即像一面牆武裝起來,這是很危險的,這面牆防止觀者穿越、體會更深邃的藝術層面。或許也不需要"穿越",作品要表達的,也許只是點子與技術而已。如果成立,作品是沒有重點的,若有,也只是示範技術和展現點子,對觀眾而言絕無影響,但對創作者別具意味。為了藝術的價值,觀者必須能夠體會和感覺作品的深度。在創作過程裡,對藝術家而言,首先應該將所有的自我感去除,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,正也呼籲了郭的作品。
她說:「在我的作品裡,思想是一扇通往創造道路的大門,而創造力的起源首先必將思想停止。德國哲學家尼采曾說:「當夜在最幽靜的時刻,露水便落在小草上。」以及「思想的到來,就像鴿子靜悄悄的腳尖,領導了世界。」像尼采一樣,我相信當心靈最平靜的時候,真理則顯現。
「這份寧靜反射在我創作的過程中。作畫時,先將腦袋淨空,準備進入一個安靜的情境。我意識到自己的身體與心靈充滿了一股非凡能量,帶領我走向創作領域;只跟隨但不思考、分析、批評及註解。此時,畫面開始一一顯現影像,讓我看見徹底的嶄新、未曾見過的東西和真的感覺。我感到栩栩如生,沒有過去或未來的臨場體驗,我相信我的作品也能和觀者溝通同樣的感覺。」
這溝通若是真的發生,會是一項可能日後影響觀者有必要做的改變。今日觀者看一件作品的標準,往往花上略短的時間,盡可能在這僅有的時間裡,看完美術博物館裡所有的作品。館內提供的語音、影像輔助工具,精確地告訴觀者應該如何看、如何想、如何感覺,其結果影響人們自己不看、不想也不感覺。
藝術是一種溝通的語言,以求讓它開展,觀者必須是第一參與者。作品不是很有必要讓觀者瞬間了解或是識別形體,但介於作品與觀者之間的互動是絕對重要。
馬克•羅斯科(Mark Rothko 1903-1970)抽象表現主義的蘇聯─美國畫家。他的抽象繪畫著名到讓觀者不知道為什麼會哭泣。而羅斯科說明觀者會產生這樣的情緒反應,其原因是因為他放入自己的情感到他的畫裡,所以觀者感覺到,其結果證實情感活絡了寂靜且不須文字溝通。
相同地,愛德華•霍普(Edward Hopper 1882-1967)寫實主義派時期的美國畫家。他說:「繪畫應該扮演宛如一面鏡子,可供人們觀看,能夠有意識,或是無意識回應,但藝術終究還是屬於人類,深厚的人性和情感。」
若我們回到經典的藝術裡,我們需要看到的藝術不是為了消遣,更不是來玩耍,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,就是為了教育人類做自己、我們居住的世界,和如何置身存活。
今天,郭的繪畫針對在看畫上提出方法,那就是要求觀者花些時間沉澱及感覺作品,許諾自己走近並超越藝術的深沈面,進行溝通對談。
如馬克•羅斯科和愛德華•霍普,郭的藝術語言是觸景生情而不是蓋棺論定,有太多詮釋作品的方法,皆仰賴作品如何被解讀和觀者以何種心情來欣賞,故此給人層出不窮的感覺。藝術是一個活生生的語言,而且不斷地變化。
郭說:「觀者看見我的比較抽象的畫面,反應是:這是甚麼?甚麼也沒有?如果觀者能夠花較長的時間,將會發現一種奇妙的現象─畫面從無處顯現原形的真實感。曾有觀者目睹而說:「原先的綠,下一片刻竟變成從樹影射進的陽光;藍色顯現胚胎;水綠色化成心跳。
「我是位畫家,對色彩敏感,甚多感覺,色彩是我主要構思畫面的源頭。所以,觀者若看到畫面從無處顯現原形的真實感,我不感到驚訝。我不企圖製造這種特殊效果,但是,我總是相信從觀者在看畫觀點和作者創作動機上,兩者同等重要,相互呼應。
「期許觀者在作品前不要思想、分析、批評及註解,與作品安靜相處,讓藝術能量帶領,進入永續嶄新的狀態,乃至體會強烈的感受力。我相信這股感受力即是藝術創作的核心。任何新觀點、發現將從此展開,並重新整頓我們的生活;一切的發生皆是轉變,繼而是個認識自己的新方向和我們居住的世界。」